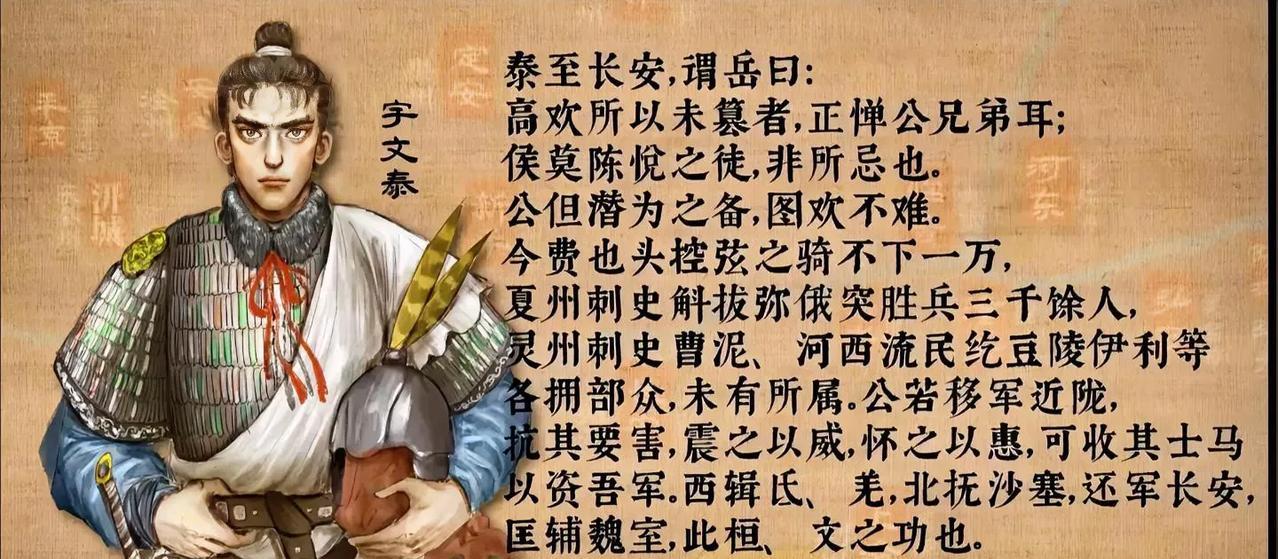1976年徐景贤进去后,在里面一直身体不好。他夫人葛蕴芳写信申述,于是徐景贤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保外就医,又于1995年刑满,1999年恢复权利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政坛,徐景贤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。 他并非依靠扎实政绩或过人才能跻身高位。 而是在特殊历史洪流中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人物。 他那会儿爬得快,倒台也挺快,像坐了个疯狂的过山车。七六年之后,属于他的政治生命基本就断送了,“四人帮”成了人人喊打的标签,作为核心圈子里的“笔杆子”,徐景贤自然难逃清算。一判就是十来年,铁窗岁月比他在台上呼风唤雨的时间都要长得多。身体不好?大概是心力交瘁,也可能是过去的风光衬得高墙内的日子更加难熬。多亏了夫人葛蕴芳在外面使劲申诉奔走,他才算提前三年,在九二年捞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。当年翻云覆雨的人物,最后得靠家人申诉、身体不行才能早点脱离囹圄。这和他上台的路子一样,都不太像是靠本事,更像是一种……嗯,命运的起伏或者说历史的特殊“照顾”? 后来出狱了,刑满了,九九年权利也恢复了。表面上看,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,但发生过的一切能真的抹掉吗?他晚年写过一些回忆文字,试图用“受时代影响”、“个人执行者”之类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过去。这就挺值得琢磨的。他承认被裹挟,承认卷入历史的漩涡,但他为自己在那些非常时期扮演的角色,究竟负有多大的责任呢?光说时代洪流,怕是不够。每一个身处漩涡中心的人,在那样的乱局中,难道真的只是身不由己的浮萍,就没有一丝一毫的主动选择?往上爬的时候那么“积极”,站队那么“精准”,执行起来那么“得力”,等秋后算账了,就把一切都推给“历史的洪流”,这逻辑是不是有点太过轻巧了? 徐景贤身上最刺眼的,还是那种巨大的反差。从一个普通的文化干部到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人物,他的飞升靠的不是真才实学、民生福祉,而是迎合了特殊时期的狂热和斗争需要;而他的跌落,也是因为站错了队,成了政治斗争失败的牺牲品。他的“成功”与“失败”,都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个人奋斗或能力展现的结果,更像是被时代抛起又狠狠摔下的标本。他的经历,活脱脱演绎了那句老话——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。整个过程中,个人的才干与贡献几乎被淹没在政治标签与时代烟尘之下。这个现象本身,就是对他那段经历最无情的批判。 徐景贤跌宕的一生,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可能是:当政治气候不正常,当提拔干部的标准脱离了常识、脱离了民生福祉、脱离了实际能力,那爬到高处的人,大概率是靠不住的。而且,当风向突变,他们摔下来也会特别狠。这种靠风口起飞的“能人”,终究只是特定时代的脆弱泡沫。个人的选择、担当和责任,即使在最混乱的时代,也不应该被轻飘飘地一笔勾销。反思徐景贤,就是反思那段特殊历史的运行逻辑,想想我们该如何避免让权力再次落入这样“身不由己”的人手中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